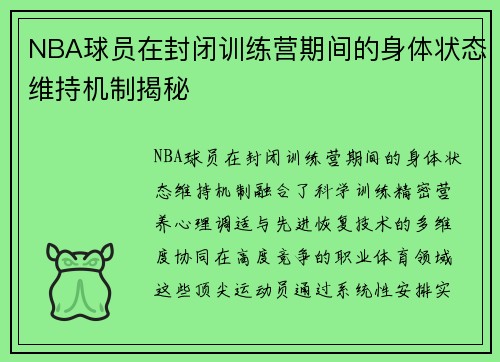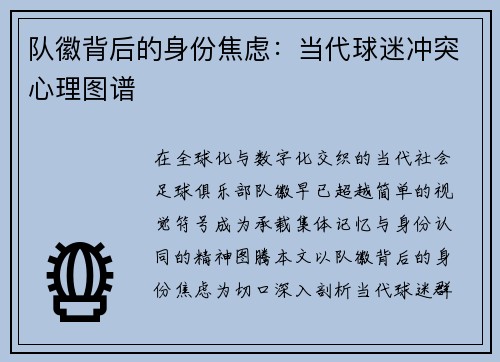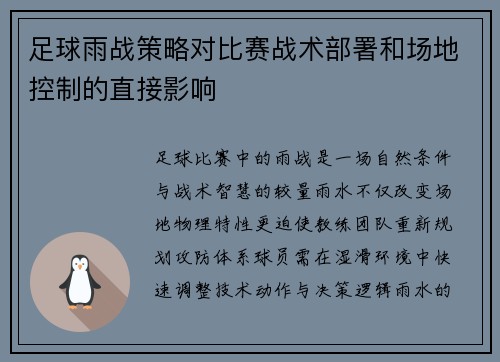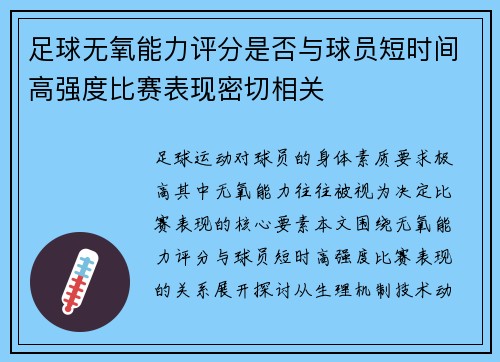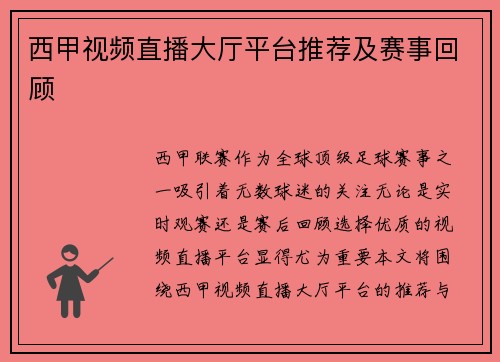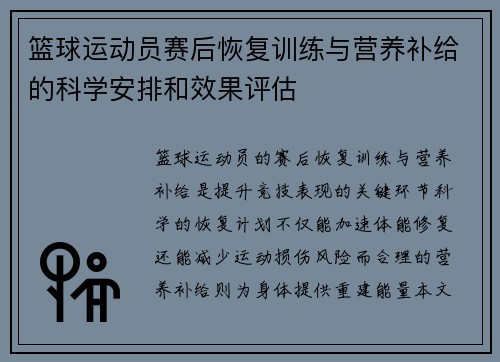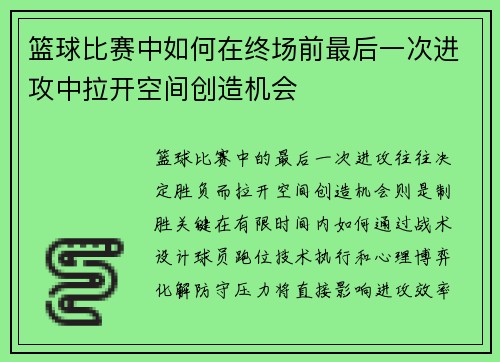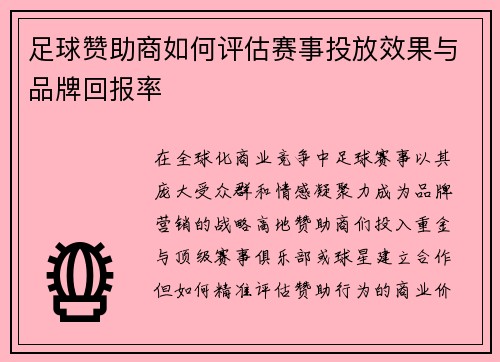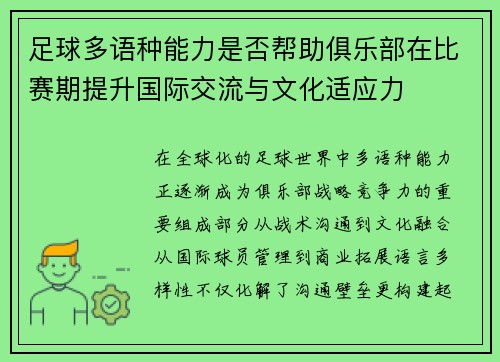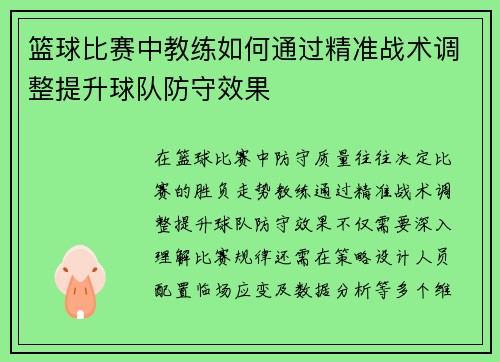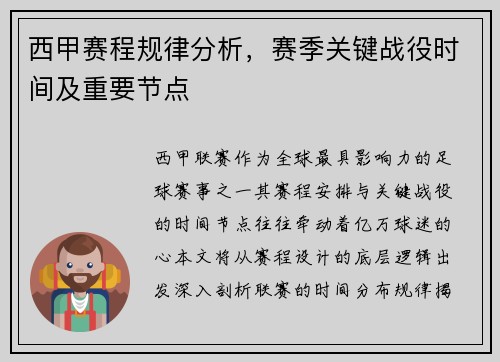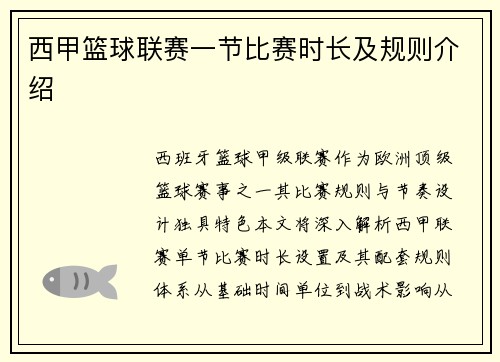中国足球超级联赛(中超)作为中国职业足球的顶级赛事,其背后交织着复杂的商业利益与行政管理逻辑。本文聚焦中超联赛背后的资本主体及其与"阎主席"(原中国足协主席阎世铎)时期形成的管理架构之间的互动关系,从企业投资逻辑、权力分配模式、商业化矛盾及未来改革方向四个维度展开分析。通过梳理国企、民企、外资等多元资本对联赛的渗透路径,剖析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间的博弈,揭示中国职业足球在全球化浪潮与本土体制夹缝中的生存现状。
一、投资方的多元角色博弈
中超联赛的资本版图呈现出鲜明的"三足鼎立"格局。国有企业依托政策资源优势深度介入,如中信集团、上港集团等通过俱乐部控股实现政企利益捆绑。这类投资往往承载着城市形象塑造、政绩工程展示等非商业诉求,导致俱乐部运营时常偏离市场规律。以北京国安为例,中信集团长达26年的持续注资创造了中国职业足球最长的单一企业运营纪录,却也暴露了国企足球特有的预算软约束问题。
民营企业投资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商业逻辑。恒大集团2010年入主广州足球俱乐部后,通过"烧钱模式"快速打造出亚洲顶级球队,开创了资本驱动竞技成绩的典型路径。这类投资虽短期内抬升联赛关注度,但长期来看推高了球员薪资泡沫,加剧了中小俱乐部的生存压力。苏宁集团投资江苏队的失败案例,则揭示了民企资本在政策不确定环境下的脆弱性。
外资介入近年来呈现新动向。红杉资本、高盛等国际投行开始布局青训数据公司、转播技术企业等产业链配套环节,卡塔尔体育投资基金更尝试直接入股俱乐部。这种"曲线救国"的投资策略既规避了政策限制,又为联赛注入了先进管理理念,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本外流、文化冲突等潜在风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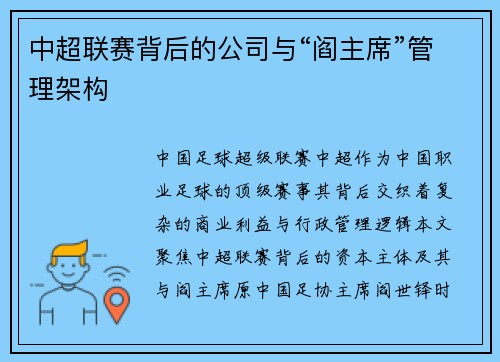
二、管理架构的权力分配模式
"阎主席时代"构建的行政主导型管理体系至今仍深刻影响着联赛运行。中国足协通过准入制度、转会规则、薪酬帽等行政手段对俱乐部实施刚性约束,这种"家长式管理"在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方面成效显著,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活力。2017年推行的U23球员强制上场政策,就因忽视俱乐部自主权而备受争议。
俱乐部联盟的自治权拓展始终步履维艰。理论上成立的职业联盟本应承担赛事运营、商业开发等职能,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受制于足协的最终决策权。2020年职业联盟筹备组提出的中超版权自主谈判方案,最终因行政干预未能落地,折射出管理权分配的结构性矛盾。
地方政府在管理体系中的隐性权力不容忽视。地方体育局通过场地租赁、安保协调、税收优惠等手段对俱乐部施加影响,形成事实上的"双重管理"格局。上海申花与久事集团的股权合作,本质上是地方政府维持足球话语权的制度性安排,这种政企合谋模式既保障了俱乐部稳定性,也模糊了市场边界。
三、商业化进程的结构性矛盾
版权收益分配机制持续引发利益冲突。体奥动力80亿元的天价版权合同破灭后,现行均分制虽保证了中小俱乐部基本收益,却削弱了头部俱乐部的创收积极性。2023赛季版权收入占比降至俱乐部总收入的28%,反映出商业开发能力的系统性缺陷。
赞助商体系存在明显的结构失衡问题。联赛总赞助金额的62%集中于酒精饮料、博彩类等争议行业,这与青少年足球发展的公益属性形成价值悖论。某啤酒品牌冠名青少年梯队选拔赛引发的舆论风波,暴露出商业伦理与足球本质的深层冲突。
k1体育十年品牌衍生品开发滞后凸显产业链短板。对比英超俱乐部平均30%的收入来自周边商品,中超该比例不足5%。广州恒大曾尝试建立电商平台直销球衣,却因物流体系、版权保护等配套缺失无疾而终。这种产业化能力的欠缺,使得联赛过度依赖资本输血而缺乏造血功能。
四、未来改革的破局路径
产权制度改革成为关键突破口。混改试点中山东泰山引入济南文旅集团,尝试构建"政府引导+市场运作"的新型治理模式。这种所有权多元化探索有助于平衡公共利益与商业诉求,但需要配套的国有资产评估机制和风险防控体系。
青训体系的商业化重构势在必行。武汉三镇首创的"足球学院+地产开发"模式,将青训投入转化为土地增值收益,这种产教融合路径虽存争议,却为破解青训投入回报难题提供了新思路。数字化青训评估系统的引入,则有望建立人才输送的标准化交易市场。
总结:
中超联赛的演进史本质上是中国特色职业体育发展道路的缩影。在"阎主席"奠定的管理框架下,行政规制与市场力量的角力始终贯穿联赛发展历程。国企的战略性布局、民企的投机性进入、外资的技术性渗透,共同编织出复杂的资本网络。这种多元主体博弈既催生了世界级转会市场的短暂繁荣,也埋下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。
面向未来,中超改革需要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治理体系。在坚持足球公益属性的前提下,通过立法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,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,完善产业链价值分配。只有实现行政监管与市场创新的动态平衡,才能推动中国职业足球突破发展瓶颈,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。